“我对世界的认识,始于荒原——地窝子巴掌大的那扇小窗,走不到边的棉花地,月光明亮的雪野,冬天的爬犁,戈壁滩的梭梭……这是新疆大地给我最早的物象。”
在作家丰收笔下,自己的童年记忆始于荒原,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兵团人用坎土曼对荒原的砍凿声开启了新疆步入现代化的进程。他的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,以下简称《西长城》),这部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,如同一部镌刻于戈壁荒原的史诗,以40万字的体量全景式展现了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壮阔历程,它不仅是一部边疆开发史,更是一部承载着家国情怀与生命韧性的“精神档案”。他将兵团的记忆、现实与未来编织成一座文学“长城”,成为解读新疆70年巨变的重要文本。

丰收在兵团团场采访。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
长城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军事防御工程,随着历史的变迁,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深处,成为捍卫国家领土安全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象征。《西长城》开篇以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尊“铸剑为犁”的青铜雕像为引,从对新疆“疆”字的解读写起,左半边一张“弓”里边护着“土”,以及新疆“三山夹两盆”的地形特征,合在一起就是“屯垦戍边”的意思。在书中,从剿匪平叛到修渠引水,从开荒造田到生态治理,一代代兵团人以血肉之躯将荒原变为绿洲,成为边疆稳定的基石。丰收笔下的“西长城”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屏障,更是兵团人“固疆守土”的精神图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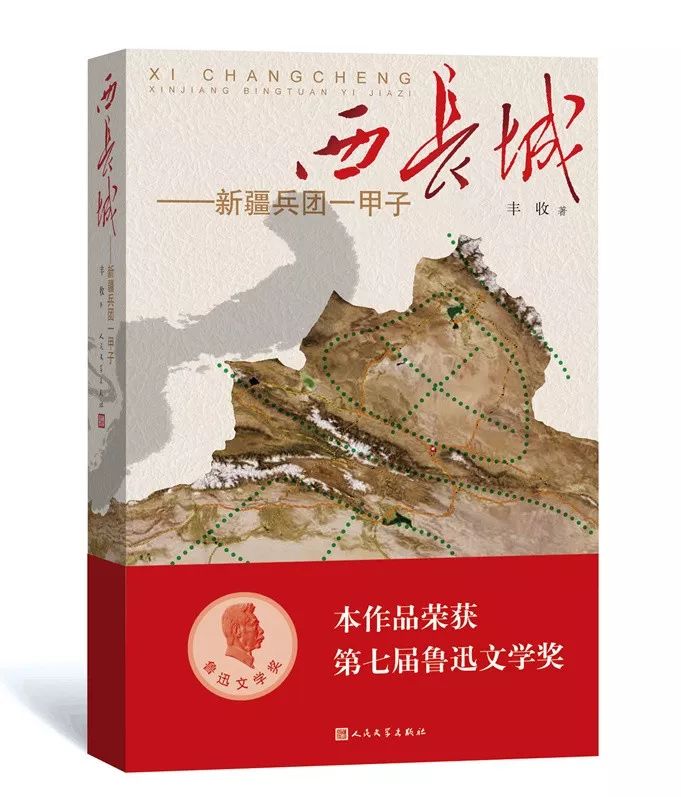
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。
“屯垦戍边本身就是一座可移动的长城,这座长城是用兵团人的青春、生命、血脉铸就的。数百万兵团人一直坚守在西部边疆,守卫祖国,就是为了国家、民族的最高利益。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,但却默默无闻,我想把他们做的事、他们的精神展现给更多的人。”这是丰收写《西长城》最朴素的初衷。
丰收是兵团第二代,也一直将写作重心置于兵团。他用几十年的创作积累,南下北上,跟踪采访了上千人,从将军到百姓,都与他们促膝深谈,留下了大量的采访记录。他跑遍兵团的每个团场连队,翻阅各种史料和新闻报道,尽可能地去靠近事件本身。“我采访过许多兵团人,他们真正视国家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,诚恳、敬业,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奉献,不计回报。作为一个创作者,我在不断选择,用最好的表现方式,把兵团人的这些特质和情怀通过《西长城》展现出来。”他说。
作为当代非虚构领域重要作家,丰收数次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、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天山文艺奖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他的作品把时代命运和个人家国发展融合在一起,展示出新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。“尊重生命,写出爱,写出人的尊严,是文学自觉的良知。”秉承这样的创作信念,丰收的《西长城》里俯拾皆是、也令人感怀至深的就是那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。他用感同身受、细腻关怀的笔触写这群在荒原上扎根,把异乡当故乡建设的普通人。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付如初对此书评述。《文心雕龙》所谓:“夸而有节、饰而不诬”,也许是因为作者采访了太多一线的劳动者,知道了太多命运无常和人生无奈,也见识了太多无名者的坚忍和牺牲,他的笔下没有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抽象的忧思,而是充满了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的朴实的“人民性”。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躯唤醒了荒原,用一生的血汗滋养了戈壁,“老兵不死,他们只是慢慢离开……”当文字记录下这些无名英雄的离开,他们已经和丝绸之路、林公车、左公柳、和艾青的诗……一起变成了新疆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组成部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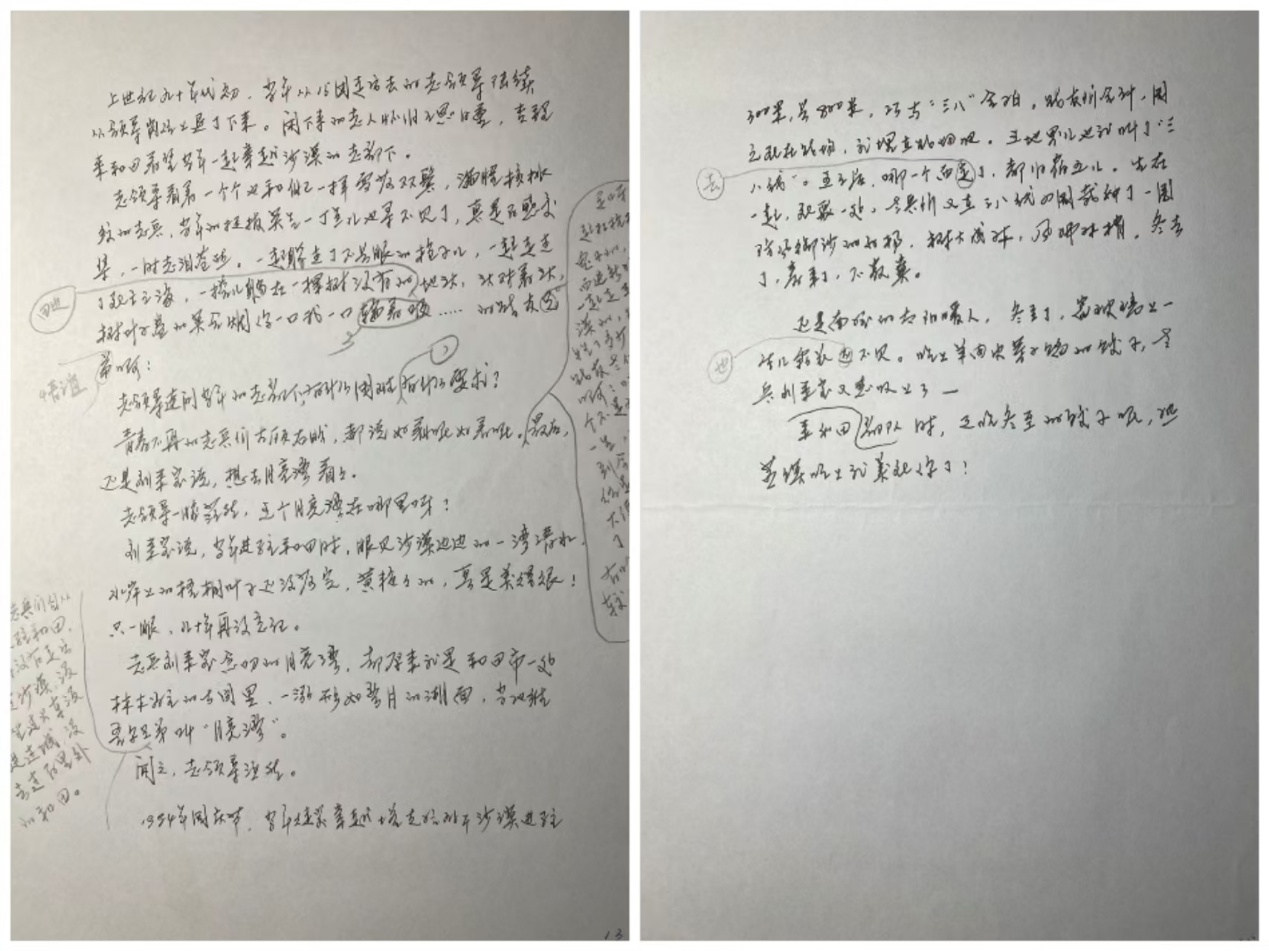
丰收《西长城》手稿。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
“《西长城》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,也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,是一本生命与信仰血肉相连的、苍茫阔达的书。对兵团人来说,信仰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和困苦,支撑他们的内心。信仰是时代永恒发展、历史永恒轮回的精神底蕴,甚至,它是历史的各种淘洗和时代的各种筛选中唯一能够留下来的真实。”评论家孟繁华说。
在《西长城》后记中,丰收写下这样的文字:“在阿拉尔,我去过一方老兵叫作‘幸福城’的墓地。这块墓地很大,塔里木最早的拓荒者先后都集合在了这里。高高的白杨林环绕着的墓地,荒草覆盖了一座挨着一座的坟头。坟前立的碑,或是一块枯裂的胡杨木板或一截水泥残桩,许多坟前连这些也没有,也是天地给予的大气了!西沉的夕阳里,我祈祷上苍记住沙土下的男男女女,佑护沙土上的众多生灵。他们仍在追求幸福。一片片荒原苏醒了,一批批人倒下了……”
兵团人的墓地以条田序号命名,他们生前焐热了土地,死后与渠水、林带融为一体。就是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生存态度,让人们看见今天的石河子、阿拉尔等兵团新城,已从“军垦第一犁”的起点蜕变为现代化的片片绿洲,看见新疆从荒芜走向繁荣的现实。而《西长城》则成为记录这场巨变的“精神坐标”。
涉深水者得蛟龙,丰收用文字为兵团立传,为边疆铸魂。《西长城》用它厚重的份量告诉人们,新疆的巨变始于一群人的坚守,而这份坚守,终将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河。













